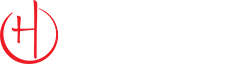苍白爆皮的嘴唇占据了额头的位置,原本的下巴上,长了一对耳朵,两只眼睛并排,取代了鼻子……
尽管被镜陵道长突击补课强大精神方面的知识,恐怖怪异的一幕,还是叫出了声。
“喔?”宋岐伯眉头轻皱,带上老花镜,示意张柏锋起开,认真的观察起来。
镜陵道长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,朝我叹了口气,说:“混账小子,又丢了我的脸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最简单不过的挪移术式,这事完了滚回山,给我恶补。”
宋岐伯检查完毕,对镜陵道长说:“别怪小全,就跟你能耐似的。五十年前咱们下陵墓,你不是被套着衣服的黄皮子吓得尿裤裆。”
“噗嗤!”我真没憋出,笑出了声。
镜陵道长急眼了,“臭庸医,老子说过多少次了,别提那件事,你他妈找打是吧!”
“要打啊,先把老张的事处理完再说。”
宋岐伯不理会发毛的镜陵道长,转头对我说:“小全啊,交给你了。我暂且能让她恢复原貌,仅仅是暂时的。虽说老张做了亏心事,也付出了代价。人啊,哪有不犯错的时候,你说呢?”
“呃……您说的对。”
我不明白宋岐伯为什么用劝说的口吻来说出这番话,好似张柏锋亏欠的我一样。
宋岐伯带女孩离开,我问张柏锋,她变成这幅模样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
“三个月前,她迷上了钢琴,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钢琴师傅。女孩子多点爱好是好的,我们也就同意了。可万万没想到,她竟爱上了那个人。当然,如果是正常恋爱,我们也不会阻拦。偏偏那人底子不干净,又是一个外国人,不得已,我只能出手拆散了他们。那人临走之前,给了她一架白色钢琴。也就是第二天,她就……哎!”
大致了解情况,我对他说:“麻烦您在家中预留一间空房,我想未来几天,会跟您同吃同住。”
张柏锋很激动,“可以,完全没有问题。”
不大一会儿,离开的两人回来。
女孩的样貌已经复原,脸上挂着兴奋和喜悦。宋岐伯就憔悴许多,竭力保持的年轻容貌,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
镜陵道长又开始怼了起来:“破个挪移术式就累成这样,你真是白活了啊。”
“你要是能破了,哪用得着我。”
两人急头白脸的掐到一起,我送张氏爷孙离开,回了房间。
百无聊赖,给青瞳打去了电话,几天不见,心里还怪想的。
响了两声,心里感觉不对,又挂断了。
从镜陵道长提出要我们结为夫妇的那一刻,我和青瞳之间的氛围,就被破坏掉了。
孰料,青瞳把电话打了回来。
“打就打,干嘛要挂断。咋滴,无法面对我了?”
她还是高高在上的态度,一句话就拆穿了我的小心思。
我说没有,按错了。
“骗你的鬼去吧,你肚子几根花花肠子,老娘闭着眼都数的清楚。”电话那端有点盲音,我听着她好像在跟谁打招呼。
心里没来由一酸,讷讷的说:“在外面吗?”
“一回家老头子就安排相亲,烦都要烦死了。你在哪呢?”
“上京。”
青瞳惊讶的说:“你来上京了,提前不给我打招呼。”
“我是被你师傅强拉硬拽来的,在宋岐伯伯伯家里。”
青瞳突然大喊:“告诉宋清梁那王八蛋,敢在骚扰老娘,我割了他命根子。先不说了,在上京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听着话筒内的盲音,我苦笑不已。
宋清梁,不用说,一定是宋老的孙子了。
上床,睡觉。
第二天,吃罢了早饭,张柏锋就开着来接我。
和镜陵道长与宋岐伯打了招呼,前往张柏锋的家中。
尽管羲皇珠宝遭受重大打击,张柏锋这些年攒下的钱足够奢侈的过一辈子。
一进别墅,什么常青藤、万古松、招财树等等,琳琅满目,我还以为进了花卉市场。
她孙女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,从楼上下来,温柔的叫了一声张哥哥。
声音酥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,还是知书达理的女人好哇。
爷孙两人先陪我在别墅转了一圈,斩煞印在山上就被镜陵道长给擦干净了,说是要考验我的洞察力,不能走捷径。
没有了斩煞印辅助,一圈下来,真的没发现啥不对劲的地方。
只能说张柏锋的关系的确挺硬,那些植被花卉,除了贵之外,摆放也很讲究。
大多是按照五行八卦,对整体运势有很大提升。
“带我去看看那架钢琴。”
我没有怀疑对象,只不过对于巧合,很是在意。
张晓兰,张柏锋的孙女,她瞬间黯然神伤,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。
一见孙女哭,张柏锋就软了下来。
“都是爷爷不好,你就不要生我的气了。”
张晓兰擦擦眼泪,对我勉强一笑,说:“钢琴在我的卧室。”
这是一架通体白色的钢琴,样式古板,缺乏新意。若非要找一个优点,那就是白,白的亮眼。
用手摸在上面,滑滑的,凉意阵阵。
我顺势坐在钢琴前,按了两下琴键。
“滴……叨……”
声音不是那么清脆,相反很沉重,音入耳,莫名的,我的情绪陡然转入悲伤。音毕,淡淡的忧伤消失一空。
尽管只有一瞬间,还是被我抓住了。
反观张柏锋和张晓兰,浑然不受钢琴的影响。
我皱了皱眉头,开始转移话题,问他关于这架钢琴的来历。
张晓兰叹了口气,说:“这架琴,是我在出国的时候,在一个小摊上买的。当时看到它的时候,就被吸引。我要买下的时候,他就出现了。他说,琴是有灵魂的,只有足够的了解琴的思维,才能奏出最美妙的曲子。”
“之后呢?”
张柏锋替张晓兰说:“之后我跟您说过,张先生,咱们略过可以吗?”
我点点头,把背上的包解下来,从中拿出一把刻着我名字的菜刀,郑重的说:“张先生,赊一把刀吧。”
严格意义上,这是我第一次赊刀。
镜陵道长把此事全权交给我,真正的目的,或许就在此。
因为我除了赊刀,没有其他的本事。
按照我所说的步骤,张柏锋面露虔诚,伸手接过刀的那一刻,我身体中所有的气尽数的往头上涌。
双眼开始肿胀发热,眼前精光一闪,奇怪的画面在我眼前出现。
漆黑的深夜里,皎洁的月光洒进了卧室。
张晓兰坐在钢琴前木讷的弹奏着,钢琴的左侧,张柏锋跪在地上,头抵着钢琴,俨然是死了。
张晓兰的手指每按过一个琴键,从琴键的下面,一缕缕黏稠的红色液体流淌出来。
画面到此终止,我面露思索,缓缓的说:“月圆之夜,白霜红缕,张叔叔,恐怕您……”
后面的话,我没有说出来。